確定回歸港股后,百度3月12日開始招股,3月16日截止融資認購。3月22日早間消息,百度在港交所發布公告稱,在香港面向散戶發售的股份已獲得逾112倍超額認購。
百度此番遭熱捧,也因為其發行價的252港元,實在是留足了上漲空間。這一價格當然參考了百度在美股的表現。與其他一些從美股回歸的中國公司一樣,從“被低估”到“受熱捧”,百度不是第一個,也絕不是最后一個。
2020年被媒體戲稱為“中概股回歸元年”。僅在6月,網易、京東便相繼掛牌港交所。而在2020年之前,小米、美團、阿里等,也紛紛已在港股二次上市。
對科技公司回歸風潮的探究已是老生常談。許多評論認為,港股2018年推出的上市新規打開了回歸的方便之門;此外,美國去年針對性明顯的《外國公司承擔責任法案》,人為地創造了這種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環境。
但是,即便美國沒有露出明顯的敵意,美國市場對于“中概股”,又真的好嗎?百度,以及百度為代表的各路中概股在美國遭遇的危機,不僅是暫時的,更基于美國投資者對“中國價值”的長期誤判。
1.價值認定,堪稱悲劇
“百度被低估”這個標題,在中文媒體早已成了月經。雖然中國投資者對百度的判斷是復雜的,但“百度被低估”這事兒,大家又都知道。
畢竟股價是一個客觀的數字。2011年,百度市值超越騰訊,但這幾乎是百度在美股的最后一次風光。彼時,百度的市值突破300億美元,市凈率一度來到30倍左右。而在2011年過后,這個數字想回歸到兩位數,都是難上加難了。
至于近年,百度的PB(市凈率)甚至只能在1到2之間晃悠。2019年,百度的資產規模,比起2011年已增長了數十倍,然而市值仍停留在300多億美元。凈資產雖然大幅增長,市值卻原地踏步,結果就是百度的PB一度低至1.36。去年就更糟糕了,隨著股價跌破90美元,百度的PB甚至低到了1.31,令人咋舌。
虎嗅頭條文章《百度成價值洼地》中稱,“百度核心業務(即剔除愛奇藝)自有現金流(凈利潤減資本性投入)始終為正”,“自有現金流充裕,公司生存無虞,研發投入不減”,未來本應“值得期待”。但與此同時,百度的股價雖然“利空出盡”,從82美元“大漲”到116美元,PB也僅有1.5倍……這個數字遠低于美國傳媒行業通常水平,更不要說互聯網了。
這不得不令人撓頭。市值比凈資產沒高多少,很難讓人相信這是一個掛著“人工智能”“自動駕駛”等鮮亮標簽的巨型科技企業。
不熟悉百度的中國網民,可能會認為百度空有龐大體量卻坐吃山空,這同樣是一個誤判。不僅市凈率(市值/凈資產)極低,百度的市銷率(市值/主營業務收入)同樣低得離譜。這當然不是因為搜索業務“回光返照”,只能說明百度的市值實在是太低了。
有人說,百度的廣告收入遭遇天花板。但其實,百度對廣告收入的依賴正在快速降低:2018、2019、2020三年,百度廣告營收占比“三級跳”,從八成到七成到六成,逐漸顯示出百度“不為人知”的其他業務的潛力。
其實百度移動生態業務的基本盤,也并沒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差。目前,百度app擁有5億的月活,而5億月活換來的想象力,就是不到2的市凈率嗎?
市值很慘的,又何止百度一家呢?被美股折磨得發狂的中國科技公司,有不少都曾像百度一樣煊赫一時。比如“時代的眼淚”搜狐,如果說百度僅僅比凈資產高那么一點兒的市值就已經很滑稽,那么搜狐從前年開始,就已經不斷在小數領域探究下限(去年已低至0.56)的PB,只能說令人捧腹。
用玩笑話說:去掉無用的公司、制度和人,搜狐直接變賣資產,所得比其市值還要高。合著搜狐公司本身的價值,居然是負的。
大哥別笑話二哥。從2018年的高峰跌落后,此時此刻,新浪的PB也只有1.1。幾乎每年都要出幾個新聞刷刷存在感,至今用戶基礎仍然非常強的攜程,PB也不到2。雖然拼多多將近20倍的市凈率確實給中概股爭了一口氣,但拼多多顯然沒辦法代表大多數中國公司。
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科技企業本就輕資產、高估值,價值全都在難以估算的“公司”和“人”上,如今零點幾、一點幾的PB,簡直是在嘲笑這個舊日理念。
更何況,美股何止會低估中國公司呢?當高估到來的時候,美股也能給你嚇一跳。
比如上周剛剛暫停交易,恐怕要沖著退市狂奔的,蛋殼公寓。
2.一個太平洋的距離
蛋殼公寓的故事已經不必再講。新鮮的是,在大洋彼岸,蛋殼的故事存在另一個版本。
2020年11月18日,每日經濟新聞發布質問,《壞消息接連不斷,蛋殼公寓股價卻突然“炸了”:一度暴漲90%,發生了什么?》。評論猜測,有傳言稱,蛋殼公寓或已找到“接盤俠”。但更多股民對此,當然是一臉懵逼的。
換我我也懵。蛋殼公寓,可以說是“成也租金貸,敗也租金貸”。很顯然,中國市場對“敗”的那一面,至今仍毛骨悚然,深感資本市場人性之惡、套路之深。但意料之外——或多或少有點兒情理之中——的是,美國市場居然看到了“成”的那一面。
為什么說情理之中?對于中國人的衣食住行,北美的媒體——尤其是財經媒體,是基本不關心的。蛋殼公寓爆雷這件事,就算跟一個中國人解釋,可能也要寫上至少幾千字才說得明白。
于是,一個大洋的時間差,帶來了一個惡毒的玩笑:當“接盤”傳言成為新聞時,曾經復雜的“爆雷”故事被北美股民拿出來研究,并被當成了“接盤”的注腳。
也就是說,當中國租客深受其害,正因為“租金貸”咬牙切齒時,事不關己的美國投資者,看到“租金貸”的模式,在短時間內居然覺得“這個模式NB啊!”
當北美股民用瀏覽器自帶的翻譯功能,艱難地閱讀復雜的爆雷新聞時,他們的反應不能說是醍醐灌頂,好歹也是欣喜若狂吧。
這是機會,機會。別人恐懼時,我要貪婪。
試圖好好解釋的中國人,被認為“你不懂”。
甚至有人認為,蛋殼的起飛干脆是揭開中國經濟起飛的幕布。結果……
感受太平洋的威力吧。
那么有沒有與蛋殼相反的故事呢?瑞幸就是最好的例子。瑞幸在美股的凄涼收場,原因其實只有四個字,“財務造假”。
其實每一個中國人都很清楚,瑞幸至今還在正常運營,關于產品和公司的新聞仍然不斷地飛著,看起來是個規模很大的連鎖企業。但在美國人眼里,不管這公司的模式如何,經營現狀怎樣,給多少中國上班族帶來了便宜的咖啡,在未來會多大程度影響中國市場的消費習慣……因為財務造假,他就必須要死,必死無疑。
而蛋殼這樣的公司,不管搞得多少中國人流落街頭,坑害了多少中國房東和租客,他都不需要退市(近日蛋殼已暫停交易,但還沒有退市)。
如果你問中國人蛋殼和瑞幸哪個更可惡一點,100個中國人里會有99個說蛋殼罪不容誅。但在美國資本市場的眼里,顯然是瑞幸“財務造假”的罪更重一些。
我們并不能說美國人傻,或者華爾街壞,這種情緒宣泄是沒有價值的。然而,一個太平洋,兩個國家,十二個小時的時差,你想讓美國人切身體會中國人的衣食住行,切身體會中國人衣食住行被攪亂時的悲傷和憤怒,確實是很難的。這就導致美股對中概股價值的判斷,存在幾乎難以消除的誤會。

此外,熟悉美股的中國股民,應該也很容易察覺雙方資本市場“價值觀念”的差別。A股的問題在于,雖然財務和運營狀況相對美股披露更詳細,但造假卻比美國嚴重得多,隱藏在數據下的彎彎繞,也讓財報變得“水很深”。
瑞幸把中國公司“造假”的毛病帶到了美國,結果被抓個正著,打得落荒而逃。造假在美國的罪孽之重,對于中國市場是難以想象的。同樣,許多美國公司在中國業務受挫,也源于他們無法理解中國的“逆鱗”是什么。中美雙方理念的分歧,不僅是歷史慣例的,金融機制的,投資邏輯的,也是政治的,甚至文化的。
甚至宏觀敘事層面,當中國成為那個“全球化秩序的維護者”時,美國卻好像拿錯了劇本,成為反全球化、反國際組織、四處“退群”的急先鋒。當這種劇變發生時,我們甚至已經見到了無來源的、不理性的反差。“凡是中國認為對的那么一定是錯的,凡是中國的人和公司那么一定是壞的”,在某些仇恨沖突中,已經悄然成為了現實。
而在資本市場,這樣的現實同樣也在發生。
3.一個概念,兩種未來
美國的投資環境,如果僅說主觀層面,對中國公司可能從來就沒有友好過。曾經的科技公司赴美上市熱潮,更多也不是因為美國“哪里好”,而是因為沒的選擇。
而在最近十年,美國的“空頭”們更是盯上了中概股。以渾水及其創始人Carson Block為例,2010至2020年初,這個“大空頭”累計做空上市公司35家,其中中概股占18家,達到一半。
空頭出現的結果是什么?除了因為“做空”導致的股價低迷,更有許多中概股被錘至退市。渾水做空的18家中國公司里,有9家已經摘牌。然而,渾水做空的公司里,也有在中國人看來基本面不錯,甚至“耳熟能詳”的公司,比如新東方和好未來,都曾面臨渾水的做空指控。
百度近日的招股書中,也詳述了渾水對于YY的做空指控。在國內,YY仍然是具有廣泛游戲用戶基礎的高活躍軟件。一些生存良好、經營正常的公司屢屢遭受做空,中國老板們,有必要重新斟酌部分美國投資者的“惡意”。
雪上加霜的是,不僅美國民間,近年來隨著國際環境和美國自身的劇變,美國交易所,甚至美國官方的態度,也從至少表面上的“客觀中立”,變成了青面獠牙、惡形惡相。
去年5月20日,納斯達克發布上市新規,要求“限制性市場”企業的IPO募資額達到2500萬美元以上,或至少達到上市后市值的四分之一。中國到底是不是“限制性市場”先不提,但2000年以來在納斯達克上市的155家中國企業中,只有40家的IPO規模超過2500萬美元。這一新規,恐怕將導致未來中國企業再難登陸納斯達克這片“科技創業福地”。
正巧同一天,美國參議院通過了《外國公司承擔責任法案》(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)。該法案要求,外國發行人連續三年不能滿足美國公眾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(PCAOB)對會計師事務所檢查要求的,將禁止其證券在美國交易。
與納斯達克新規一樣,該法案沒有“點名”針對中國企業,但是PCAOB數據顯示,其無法審計財務數據的公司中,超過95%聘用了中國的審計公司。對此,網易就直言稱,其可能無法滿足法案要求。轉過頭的六月,網易就在港股二次上市了。
2020年8月初,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表示,來自“中國和其它國家、不符合會計準則的公司”將在2021年底以前從美國證券市場被強制退市。與此同時,美國財政部在官網發布《關于保護美國投資者防范中國公司重大風險的報告》,建議針對包括中國在內的,PCAOB無法實施檢查的轄區,“提高上市門檻,加強信息披露要求,強化投資風險提示”。
喏,這回就是真點名了。總之,未來許多想赴美“鍍金”的中國公司,可能第一關都過不了。而勉強過關的,和那些已經在美股掛牌的公司,也將面臨越來越多的“找麻煩”。如果不是對于美國市場風險、成本與收益做出了重新考量,2020也不會成為中概股所謂的“回歸元年”。
對于百度來說,這種難題是兩個方向的。百度不僅是“普遍受敵視”的中概股之一,更糟的是百度做的,還全都是讓美國人敵視的業務。
美國對中國公司敵視最深的,從華為、字節、微信等近年的遭遇來看,基本是瞄準了互聯網與科技方向。百度近年的“增長點”——將要逐步取代廣告收入的那部分業務,比如云服務、人工智能、芯片、造車等,可以說每一項都要遭受美國人的冷眼,都要被美國網民怒噴“抄襲”和“小偷”。
百度已經要回來了。其實,對于這些領域有志向的公司——或者說任何對科技有點抱負的中國公司,遲早都要回來。
4.舞臺在哪兒?
2005年8月5日,百度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,隨后數年風光無兩,成為中國互聯網“三巨頭”之一。彼時,百度收獲的不僅是大額融資,更是一個屬于科技的、互聯網的窗口,是一個對外展示中國企業的舞臺。
僅僅不到20年后,百度在這個舞臺上已經淪為市值僅僅略高于凈資產的配角,沒有燈光,滿身塵埃。另一個舞臺向他招手:一個星期,473億港元,超額認購近34倍。
港股的上市新規成就了中概股的回歸,而中概股的回歸,也帶來了港交所的“第二曲線”。
“第二曲線”無論對于科技公司,對于交易所,還是對于整個中國,都是成立的。如果說曾經的中國公司一定要靠“走出去”證明自己賺了、贏了、行了,那么未來,是否只有能在“回歸”中大賺一筆的中國公司,才是新時代的“行”呢?
百度近日的招股書顯示,百度將使用約50%的募集金額用作持續科技投資,促進以人工智能為主的創新。這其實并不是什么新鮮事。近年來,百度雖然在各種費用上一省再省(2019年到2020年,除研發外的費用縮減了95億元),但研發投入是逆勢上漲的。
2020年,百度的研發費用(195億元)占核心業務收入(785億元)超過24%,占經營利潤(205億元)更是超過了95%。已經成為“價值洼地”的百度,將命運押在了未來。
未來是什么,未來的舞臺在哪里?對于云服務、人工智能、芯片、造車以及百度的“移動基本盤”,國內市場不僅是大后方,也是將來長期的主要陣地。如果美元不能感受,不能理解,無法想象中國科技企業的未來——我想,中國自己的市場,總歸能給出客觀判斷。
作者 | 天使不投資人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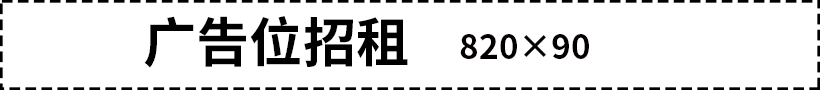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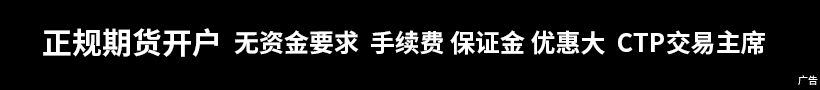
評論前必須登錄!
立即登錄 注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