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叫杜聰,出生于香港,十四歲時隨全家移民美國。
那是1980年代,作為一名隨父母從香港到達美國的新移民,杜聰在舊金山讀中學。
當時,艾滋病在美國剛剛被發現,并爆發疫情。1981年,美國男同性戀者很多相繼感染死亡。患病者通常被趕出家,丟掉工作,醫療保險也拒絕支付治療費。同性戀者被妖魔化。
這個時候,杜聰的高中老師感染艾滋病去世,從此他開始了對艾滋病的關注。這個期間,天天報紙都有刊登艾滋病的死亡人數,其中包括很著名的演藝界人士。
高中畢業后,杜聰到哥倫比亞大學完成學士學位,又在哈佛完成了碩士學位。
杜聰在哈佛大學
很多患者被歧視,大人被開除出工作崗位,孩子被開除出學校,杜聰成為了一名艾滋病志愿者。
從哈佛大學碩士畢業以后,他進入華爾街從事金融工作。
杜聰在金融界的職業發展得非常順利,在美國居住了13年后,他回到香港工作。27歲,擔任瑞士銀行駐香港聯席主席。
29歲的他當上一家投行的副總裁,正可謂當上CEO,走上人生巔峰,就差迎娶白富美了。
在投行工作時,他會到內地農村去看項目。看的是修建高速,橋梁這樣的項目,這通常是非常偏僻的地方。那是1995年,當地村民普遍都還沒有聽說過艾滋病。
1998年,杜聰與好友成立了智行基金會,做艾滋病的預防宣傳和安全套的發放。
一次他在北京參加了一個防艾會議,遇到一對從河南前來求醫的父子,從他們口中了解到,當時在我國華中地區,許多農民因貧窮去賣血,最后導致大面積艾滋病感染。
他開始擔心中國會重復美國的悲劇,于是前往當地考察。
在那里,他第一次目睹艾滋村的“人間地獄”。由于當時沒有開始抗病毒藥物的治療,一旦得了艾滋病就一定會發病死亡。
村外頭是一個連著一個的矮矮墳圈,屋里面是一雙雙絕望而痛苦的眼神,看著骨瘦如柴的孩子掙扎著在自己面前等死,杜聰心如刀絞,幾次別過頭偷拭眼淚。
這里每天都會有人因艾滋病去世,多的時候,甚至有七八個人同時離世,哭喊聲充斥著整個村子。
絕望的母親和骨瘦如柴的艾滋病患兒
在這個陰暗破敗的地方,希望是個極其稀缺的東西。
杜聰本來是想幫助這些因賣血而感染艾滋病的人,可他發現自己去的太晚,許多人已經病危或死亡。除了這些人之外,最讓他注意到的是這些艾滋病父母的孩子,他們是村里唯一的希望,大部分本身沒有艾滋病,但也受到了很多鄰居、同學甚至親戚的歧視,被貼上克死父母的不祥標簽,因為家里沒有錢,許多孩子輟學在家。
杜聰在農村和孩子在一起
本來在業余時間做志愿者的杜聰,被這些絕望的眼神抓住了,他發現,孩子們最需要的是一個重返學校的機會,因為父母們是由于貧苦無知才去賣血的,如果能夠讓這些孩子獲得學費和生活費,重回學校,就可以讓他們融入社會。
杜聰意識到,世界上少了一個出色的銀行家并不會如何,可那些孩子們卻一刻也等不了,他愿意用今天自己所有的成就和幸運去“賭”那些艾滋孤兒們的新生。
從艾滋村回來不久,杜聰便決定辭職了,全職做慈善。杜聰的母親知道后反應激烈:“我供你讀哈佛,不是讓你出來做義工的,你要做慈善,可以業余兼職去做。你現在年輕,積蓄可以供你不工作生活幾年,等你老了怎么辦?你要為你的將來著想!”
杜聰反駁母親:“將來的事我看不見,現在的事,我不能看見了不管。” 但母親認定兒子為普救眾生而選擇了自毀前程之路。
而從金融界退步抽身,眾親友意識中“阿聰是中了邪了”。他周圍的人都是一片反對和惋惜之聲。
杜聰也想過要找個既有善心又有資源,既具勇氣又懂管理,即敢擔當又能持久,既有智慧又有慈悲的人來負責基金會投入對艾滋病遺孤的幫助,但一番尋找無果,他不得不承認這個人就是他自己。
他知道覺醒是一個痛苦和孤獨的過程,可能要遭到周圍人的謾罵和圍攻,親朋好友的疏離,但只要能為那些身處苦難的人們帶來快樂和希望,自己在這個過程獲得了快樂,他認為一切就都值得。

杜聰探訪艾滋村家庭
在幫助這些艾滋孤兒的過程中,杜聰自己也曾一度抑郁,午夜夢回想到還有那么多人深陷苦海,他就被一個個悲慘故事拖至黑暗深處無法自拔,可他的內心又在不斷自我開解:“我不能因為個人能力有限就停止幫助別人,雖然救不完所有的孩子,但對于每一個幫助過的人的來說,他們的生命軌跡都可能因我們的幫助而百分之百改變。”
二十年來,他走遍全中國100多個縣,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動踐行著這一初心。
杜聰與被資助的孩子們
他一直深信,教育是影響孩子一生的禮物。
杜聰為孩子們發放助學金
孩子們參加智行基金會夏令營
孩子們的畫作
教育是最好的選擇,但也并非唯一的出路。
對于那些不想讀書的孩子,他們需要的是在社會上自給自足的技能,是把他們視為合作伙伴的平等心態,智行基金會為這些孩子提供無償法式烘焙培訓,2015年杜聰在上海創辦的Village127面包店,又為他們構造出實現夢想的平臺。這些被資助的孩子們曾在法式面包世界杯上獲得第四名,他們也在用行動來證明自己的存在與熱愛。目前Village面包店已經實現盈利,利潤的一部分會用于智行基金會的助學項目。
被資助孩子曾獲法式面包世界杯第四名
“許多社會問題的解決不一定要借助傳統捐款的慈善方式,而是可以探索更多的社會企業模式。將優質的產品或服務提供給大眾,既能滿足他們的剛性需求,同時購買的過程也可以助推公益事業,實現雙贏和可持續發展。”杜聰說。
那些賣血而感染艾滋病的人,歸根到底還是因為貧窮,所以杜聰也嘗試將社會企業模式引入到這些偏僻農村。
他在河南農村創辦了一個環保袋廠,為當地一些感染艾滋病的婦女們提供就業機會,工廠如今已經為超過100家酒店提供服務。對酒店而言,洗衣袋的供應只是運營成本的一部分,可對這些感染艾滋病的婦女來說,他們可以憑借自己的努力擁有一份體面的工作,有尊嚴地活著。
環保袋工廠的婦女們正在工作
智行基金會為孩子們捐建的圖書室
感染艾滋病的孩子
面對這些受到艾滋病影響的兒童和青年,杜聰雖然竭盡全力,但也精力有限,他可以伸手將兩萬六千多個孩子拉出深淵,可處于黑暗底部觸不可及的人更多。
隨著被救助的孩子們慢慢長大,他們也懷揣著對組建家庭的向往,智行基金會專門提供了相親服務,通過集體活動或是從資助過的數據庫里跨省介紹,目前已有68對感染艾滋病的青年步入婚姻殿堂,并借助母嬰阻斷技術,他們還生出了72個健康寶寶。
杜聰參加被救助孩子的婚禮
杜聰的臉上寫滿慈愛,雖然他自己沒有親生骨肉,但他早已將自己的生命延續到這些被救助的孩子們身上,而且他還很慶幸升級成為許多個寶寶的“杜爺爺”,看著一個個新生兒的可愛模樣,杜聰知道這是愛所延伸出的希望和善良。
“杜爺爺”和健康的龍鳳胎寶寶
杜聰和智行基金會的小伙伴們
20年來通過智行基金會,幫助兩萬艾滋病遺孤重返校園,融入社會,通過智慧的行動改變社會對艾滋病人及遺孤的歧視。
這件事不是一個月,一年,而是持續了20年。
在他的努力下,智行基金會已經成為民間艾滋救助力量中最正規、最有效的楷模。至今,他已資助了20000多個孩子,其中2510名孩子考上了大學,甚至有的考上了清華、北大,出國留學。
杜聰的家人信佛,小時候他經常目睹奶奶對弱者的行善布施,漸漸也在自己的心里種下了善的根源。
“在佛學用語里,行善布施有三種方式,第一種是財施,就像我們為孩子們交學費助學;第二種是法施,例如我們教會孩子做面包的技能;第三種是精神層面的布施,即無畏施,我們希望在智行的幫助下,能讓每一個孩子都成為一個不恐懼、無畏懼的人,讓他們能逃出艾滋病的陰影,有更多選擇的權利,重新找回生命的尊嚴,這也將會是我一生最大的驕傲。”杜聰說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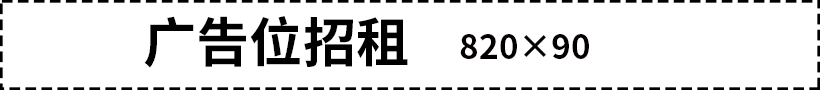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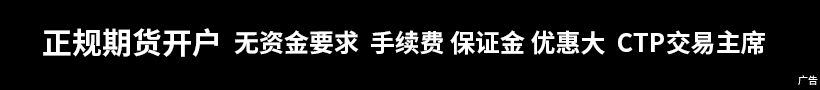
評論前必須登錄!
立即登錄 注冊